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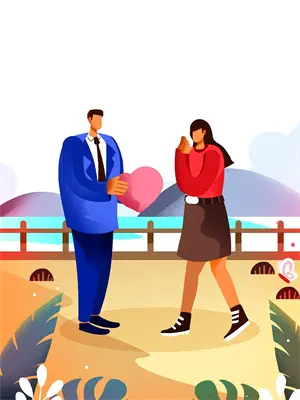
其它小说连载
其它小说《大宋女主刘娥的故事由网络作家“四郎达人”所男女主角分别是赵恒刘纯净无弹窗版故事内跟随小编一起来阅读吧!详情介绍:场数:30场时长:45分钟类型:历史/传奇/悬疑本集简介:宋太祖开宝二蜀地军官刘通之妻庞氏诞女前夜梦明月入诞下刘三日未刘通战死沙场的噩耗传抚恤金蹊跷失庞氏无力抚将襁褓中的刘娥送往眉州庞家庄娘刘娥在外婆家历经贫五岁遭邻童羞辱时初显刚十岁随姥爷赶集目睹世态炎十二岁为贴补家用街头击鼗卖屡遭地痞王二狗骚幸得张屠户与市井百姓相十三岁偶遇神秘白发老者赠《...
主角:赵恒,刘娥 更新:2025-11-11 03:23:31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场数:30场
时长:45分钟
类型:历史/传奇/悬疑
本集简介:
宋太祖开宝二年,蜀地军官刘通之妻庞氏诞女前夜梦明月入腹,诞下刘娥。三日未满,刘通战死沙场的噩耗传来,抚恤金蹊跷失踪。庞氏无力抚养,将襁褓中的刘娥送往眉州庞家庄娘家。刘娥在外婆家历经贫寒,五岁遭邻童羞辱时初显刚烈,十岁随姥爷赶集目睹世态炎凉,十二岁为贴补家用街头击鼗卖艺,屡遭地痞王二狗骚扰,幸得张屠户与市井百姓相助。十三岁偶遇神秘白发老者赠《论语》,书中夹带的半片兵符残片,与父亲遗物中的玉佩纹路暗合,让她惊觉父亲战死另有隐情。黄昏时分,刘娥凝视书卷,窗外黑影一闪而过,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
主要人物:
1. 刘娥:0-13岁。出生伴“明月入腹”异象,父亡后寄人篱下。幼时隐忍懂事,少年时以击鼗卖艺为生,容貌清秀,嗓音清亮如泉。眼神藏着超越年龄的坚韧与慧黠,十七岁因半片兵符残片对父亲死因生疑,内心埋下探寻真相的种子。
2.庞氏:25岁。刘娥之母,出身没落书香门第,通文墨,外柔内刚。夫亡后被诬陷私藏军饷,抚恤金遭克扣,被迫弃女。随身携带刘通遗留的双鱼玉佩,暗中打听丈夫死因,对女儿怀有深重愧疚。
3.姥姥:50-63岁。刘娥外婆,蜀地农妇,面容沟壑纵横,手掌布满老茧。年轻时曾随夫避战乱,深谙生存之道。对刘娥严厉却暗藏温情,深夜纺线时会偷偷给外甥女缝缀补丁,是家族的“定海神针”。
4.姥爷:52-65岁。前乡塾先生,因直言顶撞县丞被罢黜,左腿残疾。常穿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随身携带磨损的《论语》。教刘娥识字唱曲,临终前将藏有兵符残片的旧书托付于她,临终遗言“沙场月色,不照无名骨”。
5.王二狗:30-岁。华阳镇地痞,曾为粮仓看守,因监守自盗被逐。嗜赌成性,左臂有刺青“勇”字实为盗来的兵卒刺青拓片。垂涎刘娥美色与卖艺所得,多次寻衅滋事,是揭开军中黑幕的关键线索人物。
6.张屠户:40岁。华阳镇屠户,祖传杀猪手艺,左臂有刀疤实为当年从军时抵御契丹所留。性格豪爽,暗中保护刘娥,其亡兄曾为刘通麾下亲兵,知晓部分军中秘辛。
7.白发老者:60岁左右。身份神秘,常着洗旧的儒衫,随身携带青铜罗盘。实为前禁军教头,因“陈桥兵变”隐退,暗中调查军中贪腐。赠刘娥《论语》实为传递信息,其真实身份与刘通之死密切相关。
主要场景:
1.刘通军官宅邸土坯房院落,含产房、堂屋、柴房
2.庞家庄姥姥家农家小院,含正房、灶房、猪圈、老槐树
3.华阳镇集市青石板街道,含糖画摊、柴草市、屠户铺、戏台
4.永安军驻地城门、演武场、军需库废墟
5.眉州山道崎岖土路,含老槐树下、山神庙
第一场
内景·夜·刘通军官宅邸产房
蜀地成都府华阳镇,永安军驻地旁的军官宅邸。
三间土坯房拼凑的院落里,老榆树枝桠在月光中张牙舞爪,像无数双伸向夜空的手。
产房内,土墙上糊着的旧报纸已泛黄卷边,墙角陶罐里的艾草枯得发硬,苦涩气味混着产妇的汗味,在闷热的空气中发酵。
庞氏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身下的粗布被褥浸出深色汗渍,紧紧贴在她嶙峋的脊骨上。她双目紧闭,眉头拧成深褐色的疙瘩,嘴唇咬得发紫,每一次喘息都带着破风箱似的嘶鸣。
“夫人,再使劲!这胎头卡着时辰了!”稳婆跪在床前,满是褶皱的脸涨得通红。她那双常年接生的手沾着滑腻的猪油,正按在庞氏隆起的腹部,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侍女春桃16岁,梳双丫髻攥着帕子的手在颤抖,帕子已湿透。她看着主母脖颈暴起的青筋,声音发颤:“夫人,将军临走前说……说这孩子要是个姑娘,就叫娥儿,取‘月中仙子’之意呢……”
庞氏喉间溢出一声闷哼,眼角沁出泪来。她恍惚看见三天前的月夜,丈夫刘通30岁,铠甲未卸抚摸她小腹的模样——他掌心的茧子蹭得她发痒,粗声说:“北汉与契丹勾结,此战凶险。若我不归,你带孩子去眉州投奔岳父母,切记保管好我给你的双鱼佩。”
“啊——!”剧痛如潮水般涌来,庞氏猛地睁眼。 窗外,一轮圆月突然挣脱云层,清辉如银箭射穿窗棂,在泥地上投下菱形光斑。她忽然看见那月亮竟化作玉盘大小,拖着银尾撞向自己——不是幻觉!温热的暖流顺着喉咙滑入腹中,方才撕裂般的疼痛骤然消散。
“生了!生了!”稳婆猛地站起,高举着浑身通红的婴儿,脐带还连着母体。婴儿闭着眼,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哭声清亮如铜铃,震得梁上积尘簌簌落下。
春桃慌忙用备好的软布裹住婴儿,指尖触到孩子额间一点朱砂似的印记,惊得低呼:“夫人您看!这痣……像不像方才的月亮?”
庞氏虚弱地抬眼,月光恰好落在婴儿脸上。那点朱砂痣在月色中泛着微光,竟与她梦中入腹的明月轮廓分毫不差。她喃喃道:“刘娥……就叫刘娥。”
稳婆剪断脐带的剪刀“当啷”落地,春桃弯腰去捡时,忽见窗纸上映出个黑影,像只大鸟掠过长空。
第二场
外景·夜·刘通军官宅邸院落
院门外,两个黑影贴墙而立。左侧者手持令牌隐约可见“永安军”三字,右侧者腰间悬着弯刀。
“确定是今夜?”左侧黑影压低声音,喉间有痰音。 “军需官那边回话,刘通的粮草账册就藏在产房暗格。”
右侧黑影声音嘶哑,“等孩子落地,咱们就……” 话音未落,婴儿哭声突然炸响。两人对视一眼,正欲推门,忽闻远处传来马蹄声。 “巡逻队来了!”左侧黑影拽住同伴,两人如狸猫般蹿上院墙,消失在夜色中。
巡逻兵的火把在巷口晃动,马铃声由远及近。
第三场
内景·日·刘通军官宅邸堂屋
三日后清晨,阳光斜斜切过堂屋。
刘娥被裹在蓝布襁褓里,躺在铺着稻草的木箱中临时充当的摇篮,小嘴翕动着吮吸手指。
庞氏坐在木箱旁,正用炭笔在麻纸上临摹刘通的笔迹。案上摊着半截兵书,夹着一张写有“粮草亏空”的字条——这是刘通出征前塞给她的,说若他不归,便将此条交给转运使。
春桃端着药碗进来,脚步踉跄:“夫人,刚听军营传来消息,高平那边……打起来了。”
庞氏握笔的手一颤,炭笔在纸上拖出长长一道墨痕。她抓起案上的双鱼玉佩白玉质地,一鱼含珠,一鱼衔花,指尖摩挲着玉佩背面的刻字“通”。
“春桃,”她声音发紧,“去把墙根的砖挪开,把兵书藏进去。”
春桃刚走到墙角,院外突然响起急促的马蹄声,像重锤砸在青石板上。 庞氏猛地站起,撞翻了炭笔架。
第四场
内景·日·刘通军官宅邸堂屋
特写 门被“砰”地撞开,传令兵20岁,铠甲染血踉跄着闯入,披风下摆的暗红污渍在地面拖出蜿蜒痕迹。
“刘……刘都虞候家眷何在?”他捂着流血的左臂,声音因失血而发飘。
庞氏扶住摇晃的木箱,指尖掐进掌心:“我是他妻子。他……”
传令兵从怀中掏出染血的竹简,双手递上时,指节在颤抖:“刘都虞候为掩护主力……力战殉国。这是……他的遗物。”
竹简“啪”地落地,散开的竹片上,几点暗红血渍洇透竹纹——那是喷溅状的血迹,绝非寻常擦拭可留。
庞氏俯身去捡,指尖触到竹片的刹那,突然看清竹简背面刻着的小字:“粮被贪,帅不察”。
“不可能!”她猛地抬头,发髻上的银簪因动作剧烈滑落,“三天前他还说……”
“夫人!”传令兵突然压低声音,趁春桃扶他的间隙,飞快塞给她一张揉皱的纸条,“小心军需官……”
话音未落,院外传来皮靴声。传令兵脸色骤变,突然拔剑自刎——剑锋划过脖颈的瞬间,他死死盯着庞氏,嘴唇翕动着说“双鱼……”
春桃尖叫着扑到庞氏怀里,木箱里的刘娥被惊醒,发出震耳欲聋的哭声。
第五场
内景·日·刘通军官宅邸堂屋
三个身着军服的人闯入,为首者40岁,八字胡正是军需官赵虎。他踢开传令兵的尸体,三角眼在屋内扫了一圈。
“庞氏接令!”赵虎展开一卷黄绸,声音尖利,“刘通阵前通敌,私藏军粮,已革去都虞候职!其家眷即刻起抄没家产,贬为庶民!”
庞氏抱紧春桃,目光落在赵虎腰间——那枚玉佩竟与刘通的双鱼佩极为相似,只是缺了含珠的一角。
“你们胡说!”春桃挣脱开来,“将军是英雄!”
赵虎身后的亲兵一脚踹倒春桃:“放肆!”
赵虎踱步到木箱前,盯着哭闹的刘娥,嘴角勾起冷笑:“这孽种留着也是祸害……”
“住手!”庞氏突然扑过去护住木箱,“军法规定,罪臣子女年满十五方可问罪!”
赵虎愣了愣,随即笑道:“不愧是书香门第,懂的还不少。”他示意亲兵,“搜!把所有带字的东西都带走!”
第六场
内景·夜·刘通军官宅邸柴房
柴房堆满干草,庞氏抱着刘娥躲在草堆后的暗格里传令兵临死前暗示的藏身地。暗格仅容一人屈膝,空气中弥漫着霉味。 刘娥在母亲怀里吮着手指,乌溜溜的眼睛盯着头顶的木板缝——那里漏进一缕月光,像根银色的线。
“娥儿,”庞氏咬开手指,将血滴在女儿唇上,“记住这味道。你爹的血,娘的血,都是热的。”
暗格外传来赵虎的骂声:“搜仔细了!特别是那些破书烂纸!”
庞氏从发髻里抽出传令兵塞给她的纸条,借着月光看清上面的字:“岳丈家有密道”。她突然想起刘通曾说,岳父姥爷年轻时参与过修栈道,家中藏有避祸的暗室。
“春桃!”庞氏突然高声喊,“别藏了,把兵书交出来吧!” 暗格外的脚步声顿住,随即传来春桃的哭喊声:“我没有!你们别打了!”
第七场
外景·夜·刘通军官宅邸后墙
柴房后墙的狗洞被悄悄推开,庞氏抱着刘娥钻出来。她回头望了眼火光中的宅邸,春桃的惨叫声穿透夜色传来。
刘娥突然抓住母亲胸前的双鱼佩,小手指抠着玉佩的缝隙。
庞氏咬着牙转身,将玉佩塞进女儿襁褓:“娥儿,这是你爹留给你的。记住,月圆之夜,玉佩会发烫。” 她沿着墙根疾走,脚下的碎石硌得脚掌生疼。远处,巡夜兵的火把如鬼火般晃动。
第八场
外景·日·眉州山道
七日后,一辆破旧的牛车在崎岖山道上颠簸。
车板上铺着干草,庞氏抱着刘娥缩在角落,头上裹着灰布头巾。
车夫50岁,憨厚面容甩了甩鞭子,老牛“哞”地叫了一声。 “夫人,还有二十里就到庞家庄了。”车夫回头时,草帽下的眼睛闪过一丝担忧,“只是……您这银子够吗?”
庞氏从袖中摸出半块碎银——这是她变卖最后一支银簪所得。她望着车窗外掠过的野菊,声音发哑:“够的。”
怀里的刘娥突然哭闹起来,小手抓着裹布。庞氏解开襁褓,发现女儿额间的朱砂痣竟泛着红光——此刻正是正午,日头烈得晃眼。
“奇怪,”车夫凑近来看,“这痣咋会发光?”
庞氏心中一动,突然想起刘通说过的军中秘闻:“岳丈家的老槐树,树洞里藏着东西。”
她低头对刘娥轻声说,“娥儿,到了外婆家,要听话。” 牛车转过山坳,远处的庞家庄炊烟袅袅,村口的老槐树如一把巨伞,在阳光下投下浓荫。
第九场
外景·日·庞家庄村口
老槐树下,姥姥50岁,青布头巾正踮脚张望,手里的针线在衣襟上蹭了蹭。
姥爷52岁,拄着枣木拐杖站在她身后,长衫的肘部打着补丁,却浆洗得发白。
“来了!”姥姥扯着姥爷的袖子,皱纹里挤出笑意。
牛车停在树下,庞氏抱着刘娥下来时,双腿一软险些摔倒。
姥姥连忙扶住她,指尖触到她冰凉的手,眼圈瞬间红了。 “我的儿……”
姥姥的声音发颤,却在看到刘娥时顿住——婴儿额间的朱砂痣在阳光下泛着微光,像枚小小的胭脂扣。
姥爷拄着拐杖上前,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这痣……像极了当年你娘出生时的样子。”他转向庞氏,“通儿的事,我们听说了。”
庞氏“噗通”跪下,额头抵着滚烫的青石板:“爹娘,女儿不孝……” 刘娥被这动静惊醒,伸出小手抓住姥爷的拐杖头——那里雕着朵莲花,是姥爷年轻时给姥姥刻的定情物。
第十场
内景·日·姥姥家正房
正房里,灶台上的陶罐冒着热气,散发出米粥的清香。
姥姥将刘娥放在铺着粗布的土炕上,用手指逗她的小下巴。 “眉眼随通儿,这韧劲随你。”姥姥笑着抹去眼泪,转身从炕柜里掏出个布包,“这是你爹当年给我的养老钱,你拿着。”
庞氏推回布包:“娘,我不能要。娥儿以后……”
“留下吧。”姥爷坐在炕沿,抚摸着刘娥的小手,“我们庞家虽穷,还养得起一个娃娃。”他突然压低声音,“你夫家的事,镇上都在传。赵虎三天前派人来打听你的下落,说是要‘接你回营问话’。”
庞氏脸色骤变:“他们果然来了。”
姥爷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半张残破的地图,上面用朱砂圈着“军需库”三个字。“这是我前阵子去华阳镇卖柴,在废墟里捡到的。你看这笔迹……”
庞氏凑近一看,浑身冰凉——那正是刘通的笔迹!地图背面还有一行小字:“粮入私库,月黑风高”。
院外传来狗叫声,姥姥慌忙将地图藏进炕洞。姥爷对庞氏使眼色:“你从后门走,去山神庙躲三天。我自有办法应付。”
第十一场
内景·夜·姥姥家正房
深夜,油灯如豆。
姥姥坐在炕边纺线,纺车“嗡嗡”的声音里,夹杂着刘娥均匀的呼吸。
姥爷坐在门槛上,借着月光打磨那根枣木拐杖——拐杖顶端的莲花被磨得光滑发亮,里面却藏着个暗格,正是方才藏地图的地方。
“他爹,”姥姥停下纺车,“你说娥儿这孩子,将来能有出息吗?”
姥爷抬头望了眼窗外的月亮:“她额间有月,命中带光。只是这光……怕是要经些风雨。”他将拐杖靠在炕边,杖头正对着刘娥的枕头。
刘娥在梦中咂了咂嘴,小手无意识地抓住拐杖头。
第十二场
外景·日·姥姥家院子
五年后。 五岁的刘娥梳双丫髻,穿打补丁的短褂正在院子里晒谷粒,小小的身子在谷堆旁移动,像只忙碌的小蚂蚁。她手里的木耙比她还高,每推一下都要使出全身力气。
邻居家的狗蛋7岁,虎头虎脑翻墙而入,捡起块石头扔进谷堆。 “小乞丐!”狗蛋叉着腰,“我娘说你爹是叛徒,你娘是逃犯!”
刘娥攥紧木耙,小脸涨得通红:“我爹是英雄!”
“英雄?”狗蛋捡起谷粒砸她,“英雄会被抄家吗?我还听说,你娘跟军需官跑了!”
刘娥突然扔下木耙,扑过去咬住狗蛋的胳膊。狗蛋疼得大哭,抬脚踹在她胸口。 刘娥被踹倒在谷堆里,却死死咬住不放——她的目光落在狗蛋腰间的香囊上,那布料竟与赵虎亲兵的衣角一模一样。
第十三场
内景·日·姥姥家灶房
灶房里,姥姥给刘娥胸口的淤青抹猪油,疼得刘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傻孩子,打不过就跑啊。”姥姥的声音发颤,粗糙的手掌在孙女后背轻轻拍着。
刘娥咬着嘴唇:“他说我爹是叛徒。”
姥爷拄着拐杖进来,手里拿着块红薯:“娥儿,知道什么是英雄吗?”他将红薯递给她,“能忍辱负重的才是真英雄。你爹当年……”
“姥爷,”刘娥突然抬头,“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 姥爷的动作顿住,灶膛里的火光映在他脸上,明暗不定。他沉默半晌,从怀里掏出个布偶——是用刘通的旧战袍布料做的小老虎,尾巴上还缝着颗小铃铛。
“你爹像这老虎,勇猛,也……”姥爷摩挲着布偶的耳朵,“也容易被猎人盯上。”
第十四场
外景·晨·眉州山道
十岁的刘娥梳单辫,穿洗得发白的布裙牵着姥爷的手,走在去华阳镇的山道上。
露水打湿了她的布鞋,每一步都留下带水的脚印。
姥爷背着一捆柴,左腿在不平的路面上微微跛着,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
“姥爷,我来背柴。”刘娥伸手去够柴捆。
姥爷按住她的手:“等你能背动这捆柴,就真的长大了。”他指着路边的野菊,“你看这花,长在石头缝里也能开得热闹。”
刘娥看着那些金黄的小花,突然想起母亲临走时的话:“娥儿要像蜀地的竹子,能弯不能折。”
走到山神庙前,姥爷停下脚步,从柴捆里抽出根枯枝,在地上写“刘”字:“记住这个字,是你爹的姓。”
刘娥用手指描摹着地上的笔画,指尖被石子硌得生疼。
第十五场
外景·日·华阳镇集市
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叫卖声此起彼伏。糖画摊前,老师傅的铜勺在青石板上游走,转眼间画出条鳞爪分明的龙。
刘娥站在摊前,眼睛瞪得圆圆的。她的粗布裙摆上还沾着草屑,与周围穿绸缎的孩子形成鲜明对比。
“小姑娘,要个糖人吗?”老师傅笑着问,花白的胡子上沾着糖霜。
刘娥摇摇头,拉着姥爷往前走:“我们去卖柴。”
姥爷摸了摸怀里的铜板,那是家里最后的积蓄——够买半袋米,却不够买个最小的糖兔子。 他们在柴草市找了个角落,将柴捆放下。姥爷靠在墙上喘息,额角渗出的汗珠顺着皱纹滑落,在下巴汇成小水珠。
“姥爷,我给你扇风。”刘娥摘下头上的草帽,用力扇着。 草帽的影子在姥爷脸上晃动,像片移动的云。
突然,一个穿绸缎的公子哥15岁,折扇上画着牡丹撞翻柴捆,断裂的柴火散了一地。 “不长眼的东西!”公子哥用折扇指着姥爷,“弄脏了我的新鞋!”
姥爷慌忙去捡柴火:“对不住,小公子……”
“赔得起吗?”公子哥抬脚踩在柴捆上,“这鞋可是苏州绣的!”
刘娥突然挡在姥爷身前,草帽指着公子哥的鞋:“你的鞋踩了柴火,该赔我们的柴!”
公子哥愣住了,随即大笑:“哪来的野丫头?”他伸手去掀刘娥的草帽,却被她躲开。
“张屠户来了!”人群中有人喊。
刘娥回头,看见个膀大腰圆的汉子40岁,系着油腻的围裙提着杀猪刀走来,刀柄上还沾着血。
第十六场
外景·日·华阳镇屠户铺
张屠户将半扇猪肉挂在铁钩上,刀锋划过猪皮的声音清脆利落。他看着站在铺前的刘娥,递过块猪骨:“拿去熬汤,给你姥爷补补。”
刘娥摇头:“我们没钱。”
张屠户将猪骨塞进她怀里,粗声说:“拿着!我张老三送的,不要钱!”他的目光落在她磨破的鞋上,突然想起五年前那个自刎的传令兵——也是这样倔强的眼神。
刘娥抱着温热的猪骨,指尖触到张屠户围裙上的刀疤——那疤痕像条扭曲的蛇,从肘部延伸到手腕。
“张大叔,”她突然问,“你认识我爹吗?”
张屠户的刀顿了顿,猪血顺着刀刃滴落在木案上,发出“嗒嗒”声:“不……不认识。”
第十七场
内景·夜·姥姥家灶房
灶膛里的火光跳跃着,映得刘娥的脸忽明忽暗。她正在给姥爷捶腿,小手在他僵硬的膝盖上用力按揉。
“娥儿,疼吗?”姥爷问,声音里带着疲惫。
“不疼。”刘娥摇摇头,“姥爷,我想学唱歌。”
姥爷坐起身,拐杖在地上顿了顿:“学那做什么?卖艺是下九流的营生。”
“能挣钱。”刘娥的眼睛在火光中发亮,“我今天看到戏台上演戏,唱得好能得赏钱。”
姥姥端着猪骨汤进来,粗瓷碗里飘着油花:“娥儿,那不是正经出路。”
刘娥喝了口汤,烫得吐舌头:“可我想让姥爷有钱买药,让姥姥不用纺线到深夜。”
姥爷看着孙女被柴火熏黑的指尖,突然从炕洞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本手抄的《花间集》,纸页边缘已磨得发毛。 “我教你唱这个。”他翻开泛黄的纸页,“但你要记住,歌里唱的是别人的故事,脚下走的才是自己的路。”
第十八场
外景·日·华阳镇集市戏台
十二岁的刘娥站在戏台旁的老槐树下,背着姥爷亲手做的鼗鼓鼓面蒙着羊皮,柄上串着红绸。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裙,梳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系着褪色的红头绳。
“咚、咚”——她转动鼓柄,珠子击打鼓面的声音清脆悦耳。 “唱段《采桑子》吧!”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喊。
刘娥深吸一口气,开口唱道:“陌上桑间三月暮,蚕娘煮茧……”她的嗓音清亮如溪,在喧闹的集市里划出一道清澈的弧线。 阳光穿过槐树叶,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额间的朱砂痣若隐若现。
一个穿粗布短打的汉子30岁,腰间别着酒葫芦挤到前排,正是王二狗。他盯着刘娥的眼神像饿狼,嘴角的口水顺着胡茬滴落。 “小娘子唱得好!”王二狗扔出个铜板,却故意扔在刘娥脚边,“捡起来给哥笑一个!” 周围响起哄笑声。
刘娥弯腰捡铜板时,手指在袖中攥紧了姥爷给的护身木簪雕着莲花,与拐杖头同款。
第十九场
外景·日·华阳镇屠户铺
张屠户正在剃猪毛,听见集市方向的哄笑,眉头皱成疙瘩。他提起杀猪刀,刀身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张哥,又去护着那小丫头?”隔壁布铺的老板娘探出头,“王二狗可是赵军需官的远房表弟。”
张屠户啐了口唾沫:“什么东西!当年若不是刘将军……”他突然住口,提着刀大步流星地走向集市。
布铺老板娘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她记得张屠户的哥哥当年也是个兵,死在了高平战场。
第二十场
外景·日·华阳镇集市老槐树下
王二狗抓住刘娥的手腕,酒气喷在她脸上:“跟哥回府,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刘娥挣扎着,鼗鼓掉在地上,红绸被踩脏:“放开我!”
“哟,还挺倔。”王二狗另一只手去摸她的脸,“这小脸蛋……”
“啪!”一声脆响——张屠户抓住王二狗的手腕,铁钳似的手指深深掐进他肉里。
“张屠户?”王二狗疼得龇牙咧嘴,“你敢管老子的事?” 张屠户的刀背拍在王二狗脸上,留下道红印:“滚!再敢骚扰娥儿,我卸你胳膊!”
周围的人群响起叫好声。
王二狗看着张屠户腰间的刀疤那是道陈年旧伤,形状像条蜈蚣,突然想起赵虎说过的话:“避开左臂有疤的屠户,他哥是刘通的心腹。” 他悻悻地甩开手:“我们走!”带着两个跟班灰溜溜地离开。
张屠户捡起地上的鼗鼓,用围裙擦去上面的泥渍:“娥儿,没事吧?”
刘娥摇摇头,眼眶却红了——鼗鼓的羊皮面上,被踩出个黑脚印。
第二十一场
外景·黄昏·眉州山道
刘娥背着鼗鼓,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与山道上的树影交织在一起。 她手里攥着今天挣的铜板,沉甸甸的——够给姥爷抓两副药。
路过山神庙时,她停下脚步。庙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沙沙”声。
“谁在里面?”刘娥捡起块石头,警惕地问。 庙内的声音顿住。
刘娥推开门,看见个白发老者70岁,青布儒衫上打了补丁正在翻找供品。他身边的青铜罗盘在夕阳下泛着绿光。
“老人家,您没事吧?”刘娥放下石头。
老者转过身,脸上的皱纹里积着尘土,眼神却清亮如秋水:“小姑娘,你认识这东西吗?”他从怀里掏出枚锈迹斑斑的兵符残片,上面刻着“永”字。
刘娥的心猛地一跳——这残片的纹路,竟与她襁褓中双鱼佩的缺口严丝合缝!
第二十二场
内景·夜·姥姥家正房
油灯下,姥爷摩挲着兵符残片,手指在“永”字上反复摩挲。
刘娥坐在对面,怀里抱着那本白发老者赠的《论语》——书页泛黄,在第“为政”篇夹着张字条:“月照军需库,鱼佩合则明”。
“这是永安军的兵符。”姥爷的声音发颤,“当年我在乡塾教书,刘通常来借书,他说过兵符分两半,一半在主将,一半在……”
“在都虞候手里!”刘娥接过话,“张大叔说过,我爹是都虞候!”
姥姥端着油灯过来,灯光照亮她鬓角的白发:“你是说……通儿的死,和这兵符有关?”
姥爷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他指着炕洞:“地图……拿出来。”
刘娥从炕洞掏出那张残破的地图,在油灯下展开——军需库的位置旁,有个极小的鱼形标记。
“双鱼佩合璧,才能打开军需库的暗门。”姥爷抓住刘娥的手,将兵符残片塞进她掌心,“记住,月圆之夜……” 话未说完,他头一歪,靠在炕沿上死了。
油灯的火苗突然窜高,映得墙上姥爷的影子像座弯曲的山。
第二十三场
外景·夜·姥姥家院子
姥爷的葬礼在三日后举行。
一口薄皮棺材停在老槐树下,没有墓碑,只有姥姥用红布写的“庞公之墓”四个字。
刘娥跪在棺材前,将《论语》放在棺盖上。书页被夜风吹得哗哗作响,停在“君子务本”那一页。
姥姥拄着姥爷的枣木拐杖,站在一旁默默流泪。
拐杖头的莲花在月光下泛着微光。
突然,院墙外闪过个黑影,手里拿着火把。
刘娥警觉地抬头,看见黑影在老槐树上刻了个记号——那是个歪歪扭扭的“赵”字。
第二十四场
内景·夜·姥姥家正房
深夜,刘娥坐在姥爷的书桌前,借着月光翻看《论语》。书页间夹着的兵符残片,与她贴身收藏的双鱼佩母亲留下的那半放在一起——缺口完美契合,拼成完整的“永安”二字。
月光透过窗棂,照在玉佩上。
双鱼含珠的位置,竟透出微弱的光,在纸上映出个极小的“密”字。
“密……”刘娥喃喃自语,突然想起姥爷临终前的话,“月圆之夜……” 她翻开地图,将玉佩放在鱼形标记上——月光透过玉佩,在地图上投射出另一个标记:位于永安军驻地的枯井。
院外传来狗叫声,刘娥迅速将东西藏进炕洞,吹灭油灯。 黑暗中,她听见屋顶传来瓦片摩擦的声音,像老鼠在跑动。
第二十五场
外景·夜·姥姥家屋顶
两个黑影趴在屋顶,透过瓦片缝隙窥视屋内。
其中一人正是王二狗,他手里拿着赵虎给的钥匙据说是军需库的钥匙。
“那丫头肯定藏了宝贝。”王二狗压低声音,唾沫星子溅在同伴脸上,“赵大人说了,找到兵符赏五十两!”
同伴赵虎的亲兵按住他:“别冲动,等她去枯井再说。” 月光在他们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两块丑陋的补丁。
第二十六场
外景·夜·永安军驻地枯井
十五月圆夜,银辉洒满大地。
永安军驻地的废墟里,枯井旁的杂草已齐腰深,井口覆盖着半块残破的石碑刻着“军需”二字。
刘娥穿着夜行衣姥姥年轻时的旧衣裳改的,手里拿着姥爷的枣木拐杖,站在井边。
拐杖头的莲花在月光下泛着微光,与玉佩的光芒遥相呼应。 她将双鱼佩放在石碑上,月圆的刹那,玉佩突然发烫。石碑“咔哒”一声移开,露出黑黢黢的井口。
“果然有密道!”刘娥心中一喜,正欲下井,突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小丫头,果然在这儿!”王二狗举着火把走来,身后跟着赵虎的亲兵。
刘娥握紧拐杖,退到井边:“你们想干什么?”
“把兵符交出来!”赵虎的声音从阴影里传来,他手里把玩着另一半双鱼佩衔花的那半,“你娘当年藏的粮草账册,也该交出来了。”
刘娥这才明白——母亲根本没逃,而是被他们抓了!
第二十七场
外景·夜·永安军驻地枯井
张屠户躲在废墟后,手里的杀猪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
他身后跟着几个常听刘娥唱歌的青年,手里拿着扁担、锄头。
“张大叔,真要跟赵军需官对着干?”一个青年紧张地问。
张屠户盯着井边的赵虎,声音发哑:“我哥当年就是为了掩护刘将军……”他突然冲出废墟,大吼一声,“赵虎!你的死期到了!”
赵虎回头,看见张屠户的瞬间脸色骤变:“是你!”
原来,张屠户的哥哥当年发现赵虎贪墨军粮,被他灭口。刘通正是为了调查此事,才遭赵虎陷害。
双方瞬间打在一起。王二狗举着火把扑向刘娥,却被她用拐杖绊倒,火把掉进枯井。
“轰”——井里传来爆炸声,火光冲天而起。
原来井里藏着刘通当年埋下的火药,本是防备契丹的后手。
第二十八场
外景·晨·永安军驻地废墟
大火熄灭后的废墟上,朝阳升起。
赵虎被压在坍塌的石碑下,手里还攥着那半块双鱼佩。
王二狗躺在一旁,左臂的“勇”字刺青被烧得焦黑。
张屠户扶着受伤的刘娥,看着井口冒出的青烟:“娥儿,你娘……”
刘娥摇摇头,从怀里掏出块染血的衣角——那是母亲的银簪划破赵虎手臂时,带下来的布料,上面绣着半朵菊花与姥姥的拐杖头图案相同。 “我娘说过,菊花耐霜。”刘娥望着东方的朝霞,额间的朱砂痣在晨光中泛着微光,“她会等我。”
远处传来马蹄声,是朝廷派来的巡查御史——白发老者早已将证据递交上去。
第二十九场
外景·日·姥姥家老槐树
刘娥站在老槐树下,将拼合的双鱼佩挂在树枝上。玉佩在风中轻轻摇晃,阳光透过玉佩,在地上映出“忠”字的光斑。
姥姥拄着拐杖站在一旁,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娥儿,你要走了?”
刘娥点头:“御史大人说,京城有我娘的消息。”她抚摸着树干上姥爷刻的字那是她的名字“娥”,“我会回来的。”
张屠户赶着牛车过来,车上放着简单的行囊和那本《论语》。 “走吧,”张屠户憨憨地笑,“京城的路远着呢。”
第三十场
外景·日·眉州山道
牛车在山道上前行,刘娥坐在车板上,回头望着越来越远的庞家庄。老槐树的影子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个沉默的守望者。
她打开《论语》,从书页间掉出片干枯的野菊——是母亲当年夹在里面的。 刘娥将野菊贴在胸口,感受着阳光的温度。她知道,前路或许布满荆棘,但只要心中有光,便无所畏惧。
远方的地平线上,一轮新日正冉冉升起,像极了她出生那天的明月。
网友评论
小编推荐
最新小说
最新资讯
最新评论